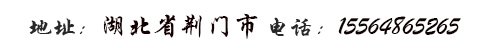悦读从刻舟求剑到盲人摸象美术史六讲
|
看白癜风不请假 http://pf.39.net/bdfyy/bdflx/180503/6210229.html 拼贴形式与复古情怀 文陆易 《从刻舟求剑到盲人摸象:美术史六讲》 年8月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点击图片即可购买) 20世纪前期,法国画家乔治·布拉克(—)和西班牙画家帕布罗·毕加索(—)在探寻立体主义时急欲突破空间限制,发明了一种新的艺术形式——拼贴(collage),拼贴是将不同的材料黏附在艺术作品表面的一种技术,并且要刻意造成画面的不和谐,各种碎片符号互相碰撞,给人一种特殊的视觉体验。步随其后的画家开始在画面上做更多的尝试和实验,直至今日,这种运用各类材质的废料重组,制成巨幅画面的艺术形式已经成熟衍化为一大艺术门类,并在艺术教育的科目中登堂入室,称为——综合媒材(assemblage)。 在中国,其实更早的时候,拼贴这种新的视觉艺术构想已经悄然在各类艺术作品中出现,并蔚然成风,只是不如在西方新的艺术风格与定义出现时那样过于兴奋和自觉。整理17至19世纪的各类关乎图像的视觉形式,在主流绘画之外的艺术样式中,总有那么特立独行的一小部分,在它们身上或多或少都能发现一些共性。譬如说对传统符号的截取,转移至另一种形式或者材质上进行运用,都有摹古的情结,会形成视觉错觉的仿真,需要观众去释读与辨别的潜在意图,等等。下面试举几例。 一、锦灰堆 元代钱选作小横卷,画名《锦灰堆》。所绘乃螯钤、虾尾、鸡翎、蚌壳、笋箨、莲房等物,皆食余剥胜,无用当弃者,文曰“世间弃物,余所不弃,笔之于图,消引日月”,加之钱选“精于花果草虫,其笔意追迹前辈,寓兴戏作残卉败叶、断枝折穗、弃谷坠翎、蚌螺蠂蠓,诸物之形逼其真,可谓妙得染色之法矣”。于是,这种被中国画坛称为“十三科”之外的杂画从此便登上大雅之堂。台北故宫博物院据说藏有他名下的一卷《锦灰堆》。 明陈洪绶锦灰堆浙江省博物馆藏 浙江省博物馆藏一件款为明代陈洪绶(—)的镜片,他在尺许方绢上画了“盖海错四、蟹钳一、爪一、海瓜子七、瓦楞子二、蛎房一,皆食余之物”(葛继常题跋语),另有“寿比南山之烛,而仅剩南山二字,是寿之余多也;又青果一,而食去其半;鼠一,啮其烛;青,东方色也,东方者,震震为长男,食其半,亦余多之意;鼠子也,谓之多男子”。葛继常还在右边题了一首诗:“催花雨过事全无,醵饮邀君酒不濡。寄与道家书一部,好将香茗著功夫。” 葛继常揣测他绘此图的用意,“观其意似为友人寿诞而作,大抵相约敛钱,备具酒肴,邀其人饮食,而其人不至,故作此图,与道家书寄之,道家书者,取其长生之意,而图寓三多之意”。一幅画内充满了隐晦的暗喻,这是古人游戏笔墨文字最擅长也最乐此不疲的事情,且留给后人无数的解读可能性,针对同一张画,须曼的题跋如下: “须曼观察得陈章侯手迹,画意诗意皆离奇,窎窅不可思议,说者以为义,取三多允矣。然予窃疑之,鼠何取乎啮烛?青何取乎谏果?海物何取乎分属?南山之烛何取乎偃踣?以意度之,殆章侯伤时之作虖,章侯生际明季,目击时艰,奄寺颛而社鼠冯陵矣,谏官放而硕果剥落矣。兵戈四海,离析分崩,南国孱王,江山半壁,玉柱一折,金瓯不完,赫赫朱明,斩马灭祀,悲夫!天心巳去,世事宁论,将餔糟歠醨,而与众人皆醉乎!宁抱朴守素而从志,松子游乎!作国之恫,既托物以写怀,招隐之思,更赋诗以寓意,所谓托旨玄妙,离尘埃而返冥极者矣!” 这便扯上了家国兴亡,老莲的政治理想落空,终究没能成为他岳父来斯行那样“有道、有学、有绩”的人,感慨“沉沦前世事,诗画此生叹”,只能在书画这类雕虫小技中倾其才华。画面中每个小物体都有各自的寓意,这是中国文化中最生生不息的传承符号。依据画面内容需要表达的情绪,选用特定的符号进行组合,还在符号上做些小功夫,比如蜡烛烧一截剩下两个字喻寿余,青果食一半意多子。观者必须去品味并具备知晓这些符号含义的基础上,才能获得其中的深意,与绘者意会,故而陈洪绶将绘事比之“作文”。 二、八破 也许出于对知识的敬畏,也许出于对文人生活的向往,也许出于对文字的憎恶,有这么一类画,另辟蹊径,经画家妙手演化,流传于民间,以致一页旧书笺、半张残帖,甚至因水渍、火熏、虫蛀的破卷残书、公文、私札、契约、函件等莫不入画。美国学者白玲安(NancyBerliner)曾撰文讨论过这一类艺术形式,她认为中国汉字有很多同音同义的异形字,比如“岁”通“碎”、“吉”通“集”,再加上画家喜欢在字面上和视觉上寓隐双关意图,这在此类绘画的命名上体现得很明显。她用了一个在北京普遍被接受的称法——“八破”。 “八破”中的“八”字是虚词。含有多、富、发等多重含意。“破”虽然是指残破的字画书笺,但隐喻了“破家值万贯”,“岁破吉生”的意思。“八破”要画出纸质类物品破碎、翻卷、重叠、玷污、撕裂、火烧和烟熏等古旧样貌,这与之前提到的“锦灰堆”多少有点同名歧义。“锦灰堆”描绘的对象是自然生长或农家养殖之物,或瓜果,或花卉,即所谓“折枝花果堆四面”,明人称之为锦盆堆,只是展现在画面上的时候,这些景物多半残缺不完整。而“八破”则是与文字有关的文化遗存,或竹简古币,或字画拓片,这是在题材上的歧义。 我曾写过两篇文章《从余集款作品探讨早期八破画的特征》和《视觉的游戏——六舟〈百岁图〉释读》分别介绍了两类“八破”,这两类现都藏于浙江省博物馆。前者是绢本工笔设色,后者是拓本,这是技法上的主要区别。它们与毕加索用实物剪裁粘贴以及之后波普艺术常用的复制、拼贴手法完全不同。 清余集款八破图十开之一浙江省博物馆藏 余集(—)款的这组十张全部由画家精心描绘,逼真到差点蒙蔽了我们的眼睛。这种写实技法,充分显现出画家对实物写生的功力,但这不是以往谢赫的“六法”中“应物象形”和“传移模写”对所绘对象的要求。这种描绘对象的真实,体现在折起的纸片,挖空烧残的画幅,被覆盖的扇面等物件的瞬间视觉真实。作品中用的明暗法,特别在不同纸质交叠处,扇子的折叠处以及纸本身的沿线沿边部分,都用了低染法渲染由重至浅过度,创造一种互相叠压的现场感。这或许是视觉艺术发展到17—19世纪后进入一种新的经验中。 清六舟百岁图浙江省博物馆藏 六舟(—)的《百岁图》,则是将一些碎小残缺、品种杂乱的金石小品用“拓”的手法,安排布置在一张画面上。这些拓下的“痕迹”散落在纸面上,虽横七竖八,颠倒翻转,但还算聚散有序,重叠有秩,仿佛是往昔留下的一堆“碎片”,组成了一个类似“寿”一样的字形外轮廓,六舟将其送给他的朋友严福基。不同于手绘八破,拓片不用写实技法来引发观者的怀古情绪,而是直接制造一个特殊的可以感知的“现场”。不用通过描绘去识别,而只是一种客观实在,如同蚕蛹蜕皮变成飞蛾离去,留下皮壳见证过往,给予观者无限遐想。在六舟这里,“八破”这种原本民间的绘画形式,或可称为“通俗文化”,一旦经由文人改手,则慢慢透露出纤细高雅的品位,以及文人阶层特别 “八破”的另一种趣味在于画家截取了完整的以文字或画作为形式对象的某个局部,然后移至同一画面中,进行有意识地摆放,或反转折起或互相覆盖。此种不同对象的叠加,加上本身的不完整性,再加上造成不完整性的原因是呈现物理性的“破”,所以我们看见的文字图像类内容大多需要靠仔细辨识猜测,才能知道对象完整时到底是件什么东西,过于残破的有时甚至未必能看明白。残章断简本身就给人以古朴典雅之感,加上需要进一步识读辨认,则更添一份趣味性在其中,让寄托思古怀旧的情绪得到进一步宣泄。 ▼ 来源浙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思想引领时代知识服务用户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合集#个上一篇下一篇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walengzia.com/wlzpz/10097.html
- 上一篇文章: 神農本草各藥的功效全錄建議收藏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