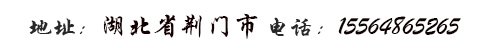当代散文女人的心愿
| 文/周德香前些日子回老家又看到了聋女人,在别人眼里她应该是个“不幸”的人,她却活岀了自己的“风采”。那天侄子开车带我去赶集,剛进菜市就看到一个穿戴整齐的女人站在一辆电动三轮车旁卖玉米,车上竖着个硬纸牌,上书:粘玉米,一元一个,十元十二个。我说:“我去买几个玉米。”侄子说:“那是咱村聋汉卖玉米,您去她可能不要钱。”是她,越活越精神了。她是六十年代末嫁到我们村的,从嫁过来的那天起大家就叫她聋汉,连她公公,婆婆,丈夫也都这么称呼:俺家聋汉怎么怎么的。她不是一点声音听不到,是听近不听远,像咱们平常说话她听不见,站在她对面大声说能听到。她有名字,那是写在证上和本上的,她来到这个村五十多年了还真没有几个知道她叫啥的。她身体健康却一生未育,娘家也没什么亲人,丈夫在本世纪初也去世了。侄子向我说了聋女人的情况:她早就是万元户了。可她还是早起晚归的干活不闲着,村里的土地转岀去后她就沟头,濠崖,边边沿沿的开荒,这里种几垅玉米,那里种爬豆,绿豆,萝卜,南瓜,茄子,豆角啥也种。八分地的院子除去住房和一条小道其余的全开成菜畦,从立夏到立冬这两季基本上是五天赶俩集卖菜。她有低保,有养老金,有残疾人补贴,有土地转让费。可是她吃穿还很节俭,连件新衣服都舍不得买。鞋也是自己做的,有人说:一双鞋二十元钱,你卖一集的菜钱就买两双鞋还做干啥。她说:“自己做的鞋穿着舒服,冬天地里没活干了我不做鞋干啥?再说别把二十元钱当小事,假如你有病住院交押金缺二十块钱人家给你办手续吗,万丈高楼是一砖一瓦垒起来的,千元万元也是一分一毛攒起来的。”“你一个人攒那么多钱干啥?”“给人家!”她大声说。大家说她精神不正常。我说:“她可能是存养老钱吧。”侄子说:“啥时代了还存养老钱,现在国家的政策这么好。没儿的比有儿的都強,有儿的想不管爹娘也没法,没儿女的国家全包,日常生活不用说,小病医生上门看,大病住院不花钱,不能动了还派专人照顾,存钱干啥”“对呀。”我说:“像她一点后顾之忧也没有真不该存钱。”“她就是个财迷疯。”侄子又说:“庄乡邻居买菜也是公平交易,一毛钱也不让,多拿她棵菜行,少给她一毛也不干。”第二天聋女人拿了六个玉米到我家来了,进门就笑着说:“婶子,听说您回来了我来看看,给你拿了几个玉米别嫌少哇。”我赶紧接过玉米说:“不嫌,稀罕着呢。”忙拿了个板凳让她坐。“咱能屋里说话吗?”她有点不好意思的说。我领她世了套间,她随手带上门说:“婶子,我想问你件事。”“好,你说吧。”“你家妹妹是在北京当医生吗?”她的脸有点微红。我点点头:“是。”“医院吗?”“噢,你是想去北京治耳朵呀?”我边说边比划。她摆摆手:“不是不是,看您想到哪去了,我都土埋到脖子的人了还治啥耳朵,我是想让她给打听着若是有耳聋的孩子家庭困难看不起病的,我,我想帮人家呀。”“啊!你想捐钱给聋孩子看病啊。”我有点吃惊。她点点头:“跟您说实话吧,这些年我攒了点钱,像我这种情况以后用不着哇,老了病了国家管,吃饭不要钱,看病住院不要钱,就连骨灰盒都给买我还要钱干啥。”我被她的想法感动的不知说啥好,一把拉过她的手说:“解荣花,你真了不起!”听到我叫岀她的名字她惊喜地说:“哎呀婶子,你咋知道我的名儿呀?”“早就知道。”我笑着说:“别忘了当初你婆婆把你的结婚证贴在墙上当画看呢。”说罢这事她急着要走说去赶集卖玉米,我把她送到大门口,她又悄悄订嘱我:“可別忘了我托你办的事呀。”“放心吧,忘不了。”我说。望着她远去的背影,不觉眼中流下泪来。(图片源自网络)《当代散文》由山东省散文学会主办,散文双月刊,主要发表山东省散文学会会员作品,欢迎山东籍散文作家申请加入山东省散文学会。山东省散文学会常年举办各种散文活动,为作家提供图书出版服务,欢迎联系。投稿邮箱:sdswxh.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walengzia.com/wlzcf/10709.html
- 上一篇文章: 认识一味中药九里香,它可用作表面麻醉
- 下一篇文章: 和而不同制礼作乐